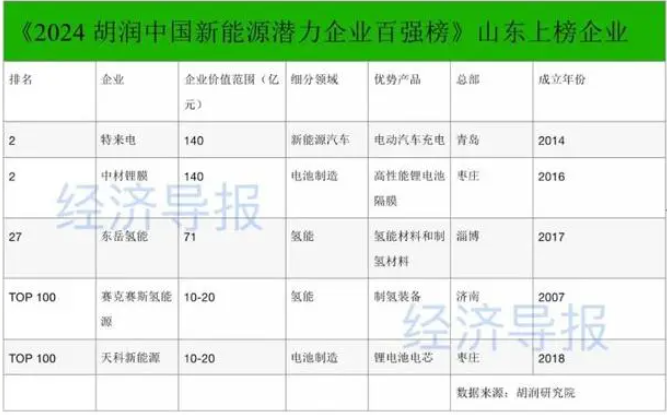“特朗普现象”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基础
近日,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办的“特朗普现象与重新认识美国”会议,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多名学者,围绕特朗普现象分三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讨论。
专题讨论(二):“特朗普现象”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基础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 图片来自网络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刘瑜副教授在《后现代化与乡愁: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文化冲突》报告中,从美国政治文化变迁的视角,讨论特朗普现象作为“果”的右翼民粹主义。她认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是一种西方世界的整体现象。如果将其视为美国特殊现象,就容易单从美国独特性寻找解释。实际上,2015年—2016年难民潮已经激起右翼势力在欧洲的普遍兴起。即便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北欧国家,同样出现了右翼民粹主义,可见不平等的加剧不足以解释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全球化的确导致了美国大量工人的失业,但不是引起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主因。大量的调查数据证明,美国并没有出现反全球化浪潮,即使是共和党内部,支持全球化的比例也是在提升的,只是提升比例没有民主党那么大。过去四十年间美国贫富差距在加大,但是美国人对贫富差距的满意度却在缩小,就政治后果而言,看法比现实更重要,这也意味着贫富差距扩大也不能解释。
刘瑜认为,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方文化后现代转型所带来的自由和保守的文化撕裂,是特朗普现象背后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本原因。现代文化社会在向后现代文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带来所谓“权利的革命”,权利的主体开始从白人男性向少数族裔、女性、儿童、移民甚至动物扩散,权利的范围不断扩大。20世纪60年代之后,右翼相对稳定,而左翼在权利革命的刺激下剧烈变动。由于权利革命的推动,实际上左翼变得越来越极端。但是之所以右翼反而会给人更极端的感觉,并不是因为其观点位置而是其观点强度发生强烈变化。右翼以一种歇斯底里的态度表达一种在历史上看比较温和的立场,而左翼是以一种温和的态度表达相对激进的变化。之所以右翼态度会变得更加激烈,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围心态,在美国人口代际变化中,年轻一代对共和党的支持率越来越低,未来不在共和党一边。因此共和党人在后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越发失落、焦虑,产生出一种对美好旧时光的“乡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梅 图片来自网络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梅,以《由“特朗普现象”引发的对美国媒体的再思考》为题,讨论了媒体在特朗普当选中所扮演的角色。她首先讲述了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与教育家约翰·杜威在20世纪20年代的论战。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著作《公众舆论》,该书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提出了“拟态环境”概念。拟态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再现,而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和加工,经过改造以后向人们所展示的环境。而传播媒介大多具有特定的倾向性,因而容易扭曲事实。拟态环境揭示了民主和舆论的困境,因此李普曼认为媒体应当由受过训练的精英掌握。杜威并不同意李普曼的观点,在1927年出版《公众及其问题》,坚持大众民主,强调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展现了对公众依靠自身处理公共事务的强烈信念。在现代互联网新媒体环境下,特朗普的当选展现了新媒体如何影响政治发展,公众又如何借助新技术影响2016年的选举,右翼民众如何利用新媒体对抗精英化左翼传统媒体,通过互联网传播各类信息甚至谣言诋毁希拉里,帮助特朗普当选。赵梅认为,中国学者要避免只是紧盯传统自由派媒体,而应当将底层右翼纳入重要的信息参考来源,顾及锈带、中西部劳工阶层的声音。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希 图片来自网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希教授以《“无选择困境”:政党政治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为题,探寻特朗普竞选成功背后的政党制度性因素。王希指出,特朗普以一个自称代表大众利益的局外人,挑战建制派利益,自费竞选美国总统,这种现象在美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其当选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美国独特的选举制度。王希创造了“无选择困境”(no-choice dilemma)概念,来描述美国选民在最后选举时面临的难题:无论是希拉里和特朗普都并非自己心中合适的总统人选,但是如果不选取其中一位,则面临自我剥夺选举权的困境。如果说无选择困境是偶尔出现的反常现象,它对民主的损害尚可容忍,一旦无选择困境成为常态,并且渗透和表现在总统、国会议员、州长、州议会议员等各层选举中,那么选举的民主性就会大打折扣,这在事实上剥夺了相当一部分的权利。美国政治学家列昂·爱泼斯坦(Leon Epstein)将这种弊端概括为“双寡头垄断体制”,选举票上固然可以出现两党以外的选举人,但是最终通常获胜者只在两党选举人中间产生。
王希认为,民主党与共和党经历了不断重塑的历程,通过灵活地应对变化牢牢把控美国政治,造成了选举僵化和政党工具化,使得政党的活动围绕成功赢得选举展开。当政治竞争变成放大的工具理性和实践之后,民主政治应有的道德和思想便会荡然无存。这种政党工具化为特朗普进入选举政治提供了入口,他加入共和党,通过违反政治正确吸引大批民众,从而赢得选举。
在学者讨论环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文莉教授就右翼媒体问题提出看法,认为很难找出一个为右翼民粹代言的媒体,特朗普的推特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刁大明就“无选择困境”提出质疑,认为在州一级层面是有实例证明可以突破两党制的。刘瑜认为,政党两极化的程度远大于社会两极化的程度,共和党之所以坚持反对堕胎问题的立场,和该问题涉及基督教观念中的生命观有关,妥协弹性很小,因此很难做出像移民、同性恋问题上的让步;选举团制度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可以保护小州利益,否则选举战场就集中在纽约、加州这些人口密集区,偏远地区选民的诉求就会被忽视;如果按照美国的长线历史来看,美国出现今天的极化政治很正常,与内战、重建到俄克拉荷马城大爆炸相比并没有那么严重,美国在用改革预防革命,以调节矛盾。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大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