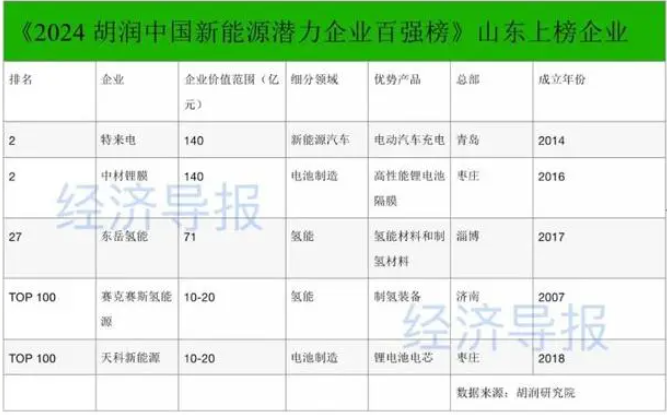刘亚秋:记忆二重性和社会本体论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有关神圣—世俗的记忆二重性是理解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一条重要线索。作为涂尔干学派的传人,哈布瓦赫真正区别和超越涂尔干—莫斯传统之处在于他提出了集体记忆概念,以群体概念具体化了涂尔干的大写的抽象社会概念,并以集体记忆的方式回应了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的基本问题,丰富了对复杂社会智识和道德问题的思考。四、哈布瓦赫与涂尔干—莫斯传统的关联通读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莫斯的《礼物》以及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著述,可以发现,哈布瓦赫继承涂尔干—莫斯传统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他对社会本体论的一贯关注。学者们也很容易从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对涂尔干的继承中得出“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是社会决定论的”这一较具批评意味的评价。
关键词:哈布瓦赫;涂尔干;集体记忆;研究;二重性;讨论;生活;礼物;社会框架;群体
作者简介:
总体上,哈布瓦赫对涂尔干—莫斯传统有所超越,但是要深入理解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尤其是其“社会框架”概念所表达的社会本体论关怀,必须要重新返回到涂尔干—莫斯传统有关观念研究的理论脉络。
进一步而言,记忆二重性概念是理解既有记忆研究的一个重要线索。尽管从1925年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概念以来,有很多学者参与到了对记忆与社会、记忆与历史议题的深入讨论,但哈布瓦赫的经典地位不可撼动。这不仅在于他开创性地提出了集体记忆概念,更在于他的集体记忆理论中蕴含的丰厚社会理论主题。但近来的多数记忆研究往往停留于将记忆作为一种方法,而不是作为一个实体。若局限于将记忆作为一种方法,则记忆研究往往停留于记忆现象的表面,即容易陷入以记忆去解释记忆的陷阱(Confino,1997),或者粗浅地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理解为记忆建构论的“现在中心观”,进而推演出记忆的权力视角(如萧阿勤,1997),或者停留于对记忆概念的形式论证上(如Olick & Robbins,1998),而对于记忆背后的文化意涵缺乏观照。当代记忆理论中颇负盛名的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也强调记忆背后的文化规则对于人们的回忆方向及现世生活重心的基础性作用,事实上是再次回到了记忆的社会本体问题,即对于记忆现象的解释不能依靠记忆这一概念,停留于诸如记忆现象的权力竞争、概念差异等问题,而需探究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这也是本文力图探究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中记忆二重性理论根源的主旨所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中存在对个体记忆的忽视,这也是涂尔干学派的局限所在。所谓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公允地讲,可作如下归纳:个体记忆归根结底是受社会影响的,而几乎所有记忆都是由社会框架来决定的。尽管哈布瓦赫曾专门讨论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甚至还讨论了自传记忆问题,但在他心目中,个体记忆的自由之于社会,恰如韦伯的个人之于现代性的牢笼。不过,哈布瓦赫对此还是带着一丝悲悯的:集体记忆的框架把我们最私密的记忆都给彼此限定并约束住了;而个体无论在风中如何舞动,都被牵扯在一根无形的线绳之中。关注个体记忆,并伸张其与集体记忆之间的种种张力,这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文主要观点曾在2014年8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现代中国公共记忆与民族认同研究工作坊”上宣读,得到孙江教授、黄东兰教授和王楠博士等师友的批评和建议;初稿在2014年10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第三届社会理论工作坊”上宣读,得到折晓叶研究员、李友梅教授等师友的点评;成稿得到两位匿名评审人的颇多建议。特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①涂尔干指出社会力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吸引”(具有培育和增强的涵义)个体;另一方面则是对个体进行控制(汲喆,2009;赵立玮,2014)。
②哈布瓦赫(2002:312)指出,社会思想并不是抽象的,社会观念总是化身为个人和群体。
③恩师王汉生教授曾引导我对“记忆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探索。先生已逝,在此谨志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