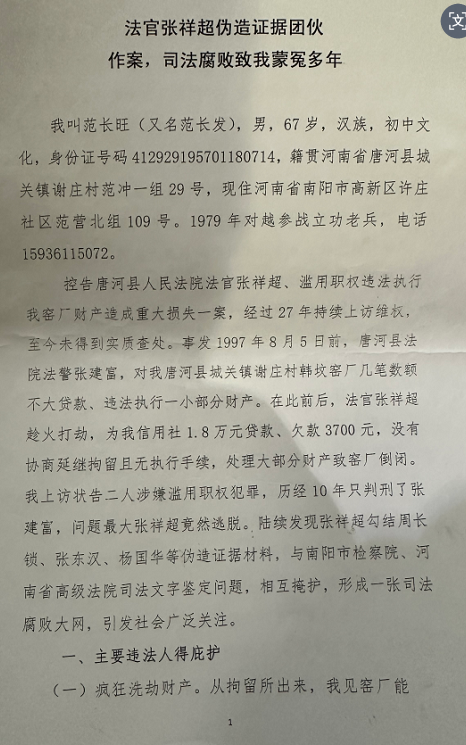邓文初:历史真实何以令人反感? | 专业视角
[摘要]从作为一种知识的历史讲,只有拥有详尽的细节,才能构筑更完备的历史叙述,建构更完整的历史场景。
作者:邓文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传统历史知识生产掌握在一个较小的知识人集团中,这批知识人(史官)具有经过严格鉴别与认证的“正统”身份,惟有他们才可以接触那些高度秘密的档案,接触一些大众难以接触的文献、文物,他们熟悉自己的行业规范,知道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也清楚圈内圈外的界限何在,什么可以公开,让公众知道;什么不可以公开,仅能在行内交流。对于他们的工作来说,与其说是在“生产”历史知识,不如说是在“监控”历史知识。
作为整个权力计划的一部分,历史知识生产成为社会控制的核心机制。在“权利的公民”没有完成的时候,已经成功完成了“历史的国民”之规训。于是,历史知识生产,便与“秩序”生产合二为一。
“多种真相”需要我们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独立思考,而非简单接受某个单一结论。然而,从“计划时代”走过来的我们,并没有做好面对知识市场的心理储备,尤其没有进行独立思考的实地练习,于是,体制外史家便成了罪魁祸首。“历史真实”不仅没有激活这个古老民族的想象力,反而引起诸多误解甚至反感,导致冲突,心理不适。
胡适在广州为何受到声讨?
1935年1月9日,从香港乘船到广州,船刚靠岸,就接到一位老朋友托人带来的信:“兄此次到粤,诸须谨慎”。胡适并没在意会发生什么不测,因为广东学界领袖都来欢迎,且四天十场的演讲日程也排得满满的。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还贴出告示全校停课两天,好让学生去听胡适演讲。

胡适
入驻酒店后,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康差人送来一信,信中说:“适晤邹海滨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
所谓既来之则安之,胡适还是去见了省主席林云陔和总司令陈济棠,且谈了一回话,双方颇有争论。此时胡适已经知道是这位“南国王”陈济棠将不利于己。回到酒店后,吴康又送一信,说“鄙意留省以勿演讲为妙。党部方面空气不佳,发生纠纷,反为不妙”。并告知胡适,邹鲁个人虽极推重先生,“惟事已至此,只好向先生道歉,并劝先生离省,冀免发生纠纷”。
为避免学界为难,胡适决定取消演讲,在广州仅做游览,然后去广西走走。晚上,得到新闻,为中山大学布告,布告解释了取消演讲的原因,谓胡适——
在港华侨教育会所发表之言论,竟谓香港最高教育当局,也想改进中国的文化,又谓各位应该把他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复谓广东自古为中国的殖民地等语。此等言论,在中国国家立场言之,胡适为认人作父,在广东人民地位言之,胡适竟以吾粤为生番蛮族,实失学者态度,应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讲。
胡适在香港究竟说了什么?他自己援引当时报纸的记载,大约有如下言论:
我觉得一个地方的文化传到他的殖民地或边境,本地方已经变了,而边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着它祖宗的遗物。广东自古是中国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许多都变了,而在广东尚留着。像现在的广东音是最古的,我现在说的话才是新的。
这不过是一篇“中心与边缘”的文化论罢,旧典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之类的陈词套语,不料却惹出这样的麻烦。不仅中山大学发布如上布告,三位国文系教授且发布宣言、启事,声称“胡适出言侮辱宗国,侮辱广东三千万人,中山大学布告驱之,定其罪名为认人作父”,且表示“夫认人作父,此贼子也。刑罚不加,直等以为遗憾”。声明要以孔子诛少正卯之手段将胡适“立正典刑”。否则,“老口北返,将笑广东为无人也”。
对于这段经历,胡适的理解是,当时主政广东的陈济棠提倡读经,而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却对读经多有批评。平时他胡适远在北平,对地处偏域的广东,虽鞭长善舞,也有莫及之憾。而现身处香港,再批评读经之类自然是一鞭即着,何况还准备在南国王脚下反对读经,岂不就惹出风波来了。

陈济棠
但这样的理解并没到位,“读经”虽由武人提倡而不免杀气腾腾,但那是不关“广东三千万人”什么事的。究其实,胡适戳中广东痛处的,是“中国殖民地”这五个字,虽然,这不过是说出了一个历史事实。但,真相却往往令人反感。
历史的“供给制”不是生产知识,而是“监控”历史
胡适故事且搁下,说说历史学界内的事吧。因为这样为“历史”而大起纠纷,报以臭鞋、饱以老拳、甚至动辄即要“立正典刑”之类的事已非胡适时代的怪事,而是我们时代的经典表情。一些历史禁区不能碰触,真相只能允许一种,异类的声音永被禁锢。历史真相为何就那样令人反感呢?
从作为一种知识的历史讲,只有拥有详尽的细节,才能构筑更完备的历史叙述,建构更完整的历史场景。而在此场景中的历史人物才可能有更完整的活动轨迹,由此历史学家们才能展现出这个历史人物有血有肉的具体而真实的形象。按理,史料越多越好,所谓“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十分材料说十分话”。现在有了更多的史料,史学家们要“说话”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从常识角度讲,这也该是件大好事。多了“一家之言”,如同知识市场多了一件新商品,消费者有了更多挑选,不同的嗜好和需求能得到满足,这本该是小康社会的基本特征!
但国人似乎并不需要这样的多样性,尤其是对于历史真实还十分反感。这样的反常事件总是“炎症”般周期发作。因此,我们需要对此做出病理诊断,以免在溃疡之后发生癌变。尽管,把脉这个“综合症”并非易事。
病因当然不在史家,主要是历史知识生产与接受环境的根本改变。
传统历史知识生产是掌握在一个较小的知识人集团中的,这批知识人(史官)具有经过严格鉴别与认证的“正统”身份,惟有他们才可以接触那些高度秘密的档案,接触一些大众难以接触的文献、文物,他们熟悉自己行业规范,知道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也清楚圈内圈外的界限何在,什么可以公开,让公众知道;什么不可以公开,仅能在行内交流。对于他们的工作来说,与其说是在“生产”历史知识,不如说是在“监控”历史知识,以保证流入社会的历史知识绝对正统,保证对这些历史知识理解的绝对精确。这种知识生产与消费是有计划的,是严格的“供给制”,不存在自由市场;是单一的“传输——接受”模式,而非“阅读——诠释”模式。

司马迁历来被视为史官典范。
在这样的“计划时代”,历史知识生产是政治动员的神器,历史记忆的建构是政治合法性基础。作为整个权力计划的一部分,历史知识生产成为社会控制的核心机制。在“权利的公民”没有完成的时候,已经成功完成了“历史的国民”之规训。于是,历史知识生产,便与“秩序”生产合二为一。而维护“秩序”,不仅是权势者的生命,更是“历史的国民”的“神圣使命”。
“历史的国民”吞食的是配给的标准食料——按照“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的趣味生产出来的——一种抽象而干瘪的“高大全”。这样饲养出来的口味自然是重口味,刻骨铭心地印在儿时的记忆中,成为一种“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感情”,神圣不可侵、崇高不可亵、威严不可触,此民族主义之真感情。但这份庄严而伟大的感情,说穿了,不过是被喂养的重口味而已——按林语堂的定义,所谓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对儿时口味的偏好——那些由供给制时代培养出来的重口味者,他们当然要维护自己的口味(这没错,这是他们的权利)。但他们同时却要消灭一切别种的口味,不容许新鲜、多样口味的出现和存在。他们当然知道,政治固然可以大一统,但感情无法勉强;历史纲要必须一致,但历史事实总有差异,所以,理上说不过去的,只好拿大词说话。于是,民族情感、国家大义等等崇高字眼,便似海水般咆哮而来,唾沫星子多了,似乎真可以“卷起千堆雪”。其功效,大约也真足以消灭他者、淹死他者、根除混乱。事实虽不胜,精神总可以来一次胜利的狂欢罢!
体制外史家为何被当做“麻烦制造者”?
然而,时代的巨变无可抗拒。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非常百姓家”,历史知识生产领域的变化,原来被“官史”垄断的地盘开始被“民史”分享,“史官”的崇高身份开始没落,与一般“史家”(“真的史家”而非意识形态专家)处在平等地位。历史研究与知识生产不再受计划管制,每个人都是潜在史家,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理解撰写、传播历史。原来严控的档案,依据《档案法》,在“公布期限”之内的,普通公民也可以调阅了(尽管还受到诸多限制);原来难以检索的文献,由于网络资源的开放,普通公民也得以像专业史家一样收集史料,有时,其史料占有程度,甚至超过专业史家。由此,普通民众已经可以像专业史家一样,在家中、在电脑桌前,对文献进行考证、对比、编排,并由此做出自己的历史解释与史学叙述,互联网又可以将这些“一家之言”迅速传播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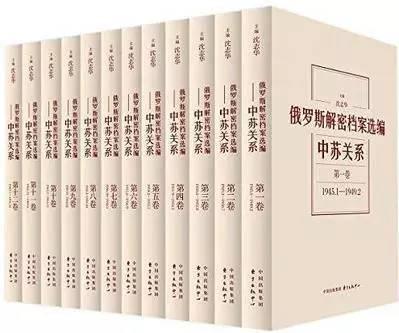
一切都改变了,食料多了、口味多了,“混乱”也随着而来。
“混乱”只不过来自更多的真相,而从独断时代走过来的我们并没有做好接受“多种真相”的心理准备,所以那些体制外史家就被当做“麻烦制造者”。
“多种真相”需要我们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独立思考,而非简单接受某个单一结论。然而,从“计划时代”走过来的我们,并没有做好面对知识市场的心理储备,尤其没有进行独立思考的实地练习,于是,体制外史家便成了罪魁祸首。“历史真实”不仅没有激活这个古老民族的想象力,反而引起诸多误解甚至反感,导致冲突,心理不适。
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这种“心理不适”来源于计划时代的大众对现代知识生产的隔膜,来源于大众无法理解“理性”运作方式与心理效果,也来源于互联网所带来的“多样共存”状态对于“单一真实”造成的颠覆性体验——人总是害怕那些他们驾驭不了的物事,多种真实并存局面对于那些习惯单一状况的心性来说,是令人恐惧的——所以,必须反对,以捍卫先前时代在心中建构起来的稳固秩序。
这就是真相令人反感的原因之一。(作者:邓文初;编辑:胡子华;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邓文初,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民国史、现代思想史、抗战史等。文备众体,以思想随笔见长。有《民族主义与国家安全》、《民族主义之旗》和《抗战总动员》之“民族主义研究”三部曲等专著及《失语的中医》、《湘西古长城考》、《谣言九论》等论文总约二百万字行世。目前正在撰写《儒教政治史稿》。
栏目简介

厚重、深远、兼容,秉持专业主义标准,汇集精英独到见解,让深刻平易近人。
腾讯思享会独家稿件,未经授权,其它媒体不得转载。
欢迎朋友们转发至个人朋友圈,分享思想之美!
微信公众号已开放置顶功能,欢迎您在本号设置页面里打开置顶开关。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